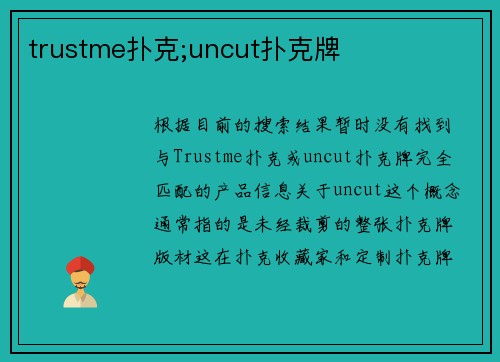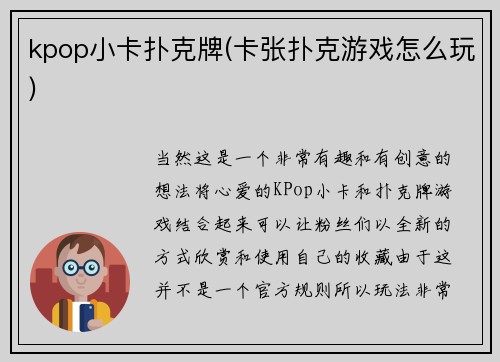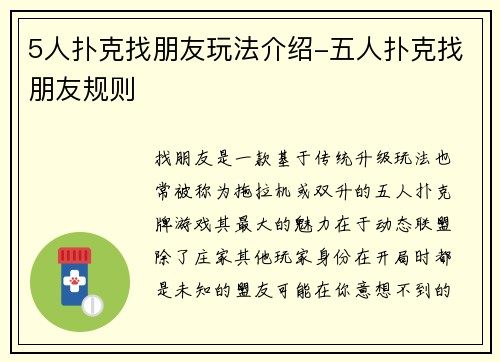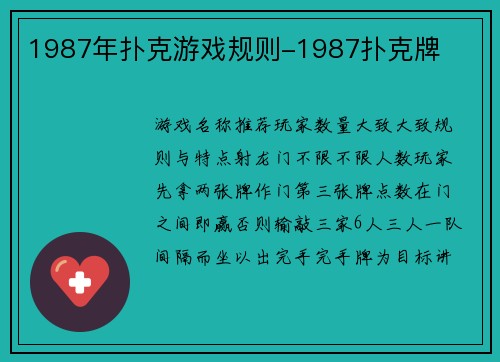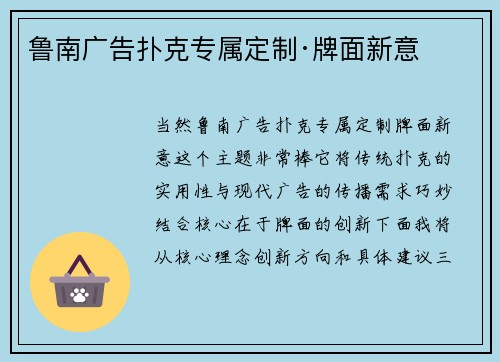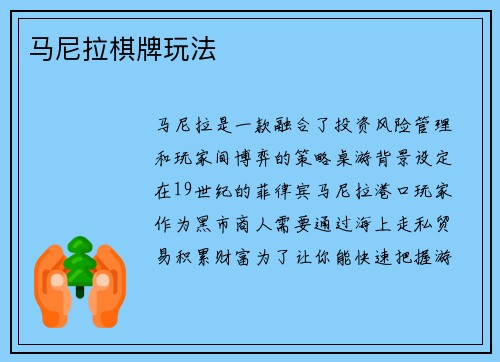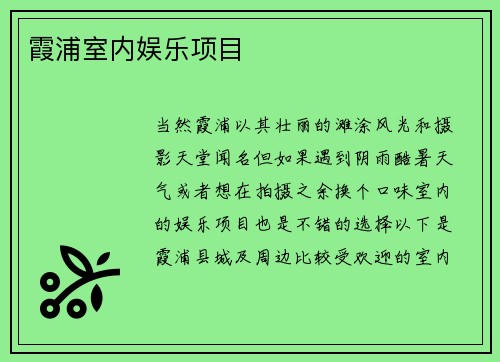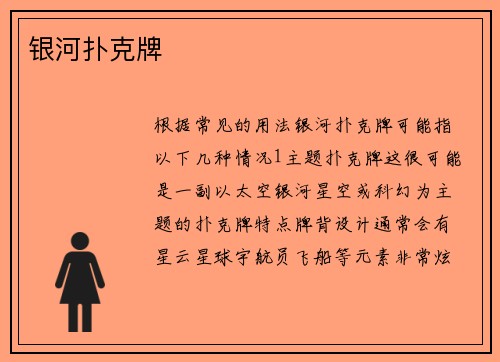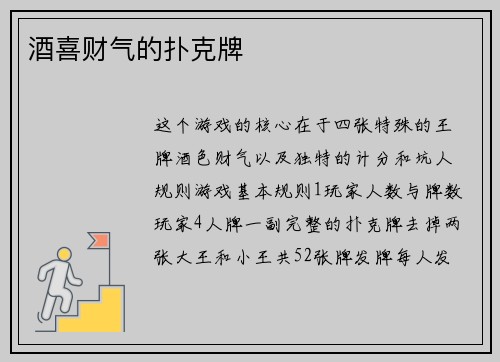>他以为自己是操盘手,掌控着两个女人的命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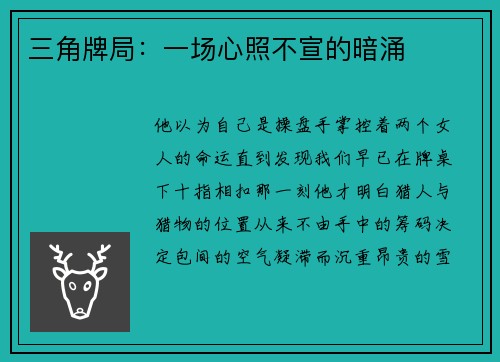
>直到发现我们早已在牌桌下十指相扣。
>那一刻他才明白——猎人与猎物的位置,从来不由手中的筹码决定。
包间的空气凝滞而沉重,昂贵的雪茄烟雾像诡谲的蓝灰色幽灵,在吊灯昏黄的光晕里盘旋、扭结。林永年喜欢这个调调,他认为这能模糊对手的判断,尤其是在这种私人牌局上。他坐在主位,身体微微后仰,食指与中指间夹着那支产自古巴的蒙特克里斯托,灰白的烟灰积了长长一截,显示着主人的从容,或者说,一种刻意维持的掌控感。
牌桌是上好的黑胡桃木,冰凉光滑的质感映着顶上唯一的光源。他刚刚推出一摞筹码,筹码,象牙或是某种合成材质,碰撞发出清脆又沉闷的声响,滚向牌桌中央。他的目光,带着一丝懒洋洋的、近乎戏谑的审视,先落在左边的苏晓身上。
苏晓,他的“自己人”。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。三年前把她从一个磕磕绊绊的新人提拔上来,手把手教她看报表、谈客户,带她进入这个流光溢彩又暗藏荆棘的名利场。她今天穿了件香槟色的丝质衬衫,领口解开一颗,露出一段纤细脆弱的脖颈,灯光下,侧脸线条柔和,低眉顺眼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牌,长睫毛在眼睑下投出浅浅的阴影。在他看过来时,她似乎无意识地用指尖捻了捻一枚绿色筹码的边缘,一个小动作,快得几乎看不见。
林永年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牵动了一下。很好。他知道她最近看中了城西新开盘的一套公寓,首付还差一些。今晚之后,那点缺口,不过是这牌桌上几个来回的事。他需要她的配合,在这局牌里,在他更大的棋局里。
他的视线随即滑向右边的沈冰。
沈冰,苏晓带来的“朋友”,一家设计工作室的合伙人,清冷,话不多,眉宇间有种难以接近的疏离感。第一次见她时,林永年就觉得这女人像一块冻住的湖面,表面上平静无波,底下却可能藏着危险的湍流。他起初有些戒备,但很快,一种更具刺激性的念头占了上风——征服,或者更准确地说,驯服。让这块冰在他手掌的温度下融化,露出依附的、讨好的模样,那一定很有趣。他试探过几次,资源,人脉,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关照,她却总是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,既不拒绝,也不靠近,像一条滑不留滑不留手的鱼。
今晚,这局牌,是他精心布置的温水。他要慢慢煮这两只青蛙,看着她们在自己的规则里沉浮,最终认清谁才是能给予一切也能拿走一切的主宰。
沈冰穿着一件黑色高领羊绒衫,衬得皮肤愈发白皙。她靠坐在椅背里,姿态放松,甚至有些慵懒,右手随意地搭在牌桌边缘桌边缘,修长的手指偶尔无意识地轻叩一下桌面。面对林永年推过来的筹码,她只是抬了抬眼,目光平静得像深潭,然后将自己面前的牌干脆地合上,弃了。
“林总手风果然很顺。”她的声音不高,带着点微凉的磁性,听不出什么情绪。
林永年哈哈一笑,顺势收回赢得的筹码,动作熟练地将它们码放整齐。“运气,都是运气。主要还是沈小姐和苏小姐承让了。”他故意把她们两人并称,目光在两人脸上扫过,试图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反应。
苏晓抬起眼,飞快地看了沈冰一下,视线相交不足半秒便分开。她拿起手边的水晶杯,抿了一口柠檬水。“是该林总赢的,”她的声音比平时稍微软一点,“牌面在那放着呢。”
荷官是俱乐部的人,面无表情地洗牌,动作精准得像机器。新的一轮开始。
牌局在继续。筹码的河流在三人之间缓慢地迁徙、汇聚、分散。林永年确实手气不错,但也并非全无波折。有两次,沈冰用不大的注额,巧妙地偷走了底池,一次是凭借河牌一张意想不到的小牌,另一次则是通过连续加注,逼得他放弃了可能更好的成牌。她的打法飘忽,时而保守,时而激进,让他有些捉摸不透。
而苏晓,大部分时间都跟随着他的节奏,偶尔在一些小池底表现出恰到好处的“挣扎”和“不甘”,最终又“无奈”地弃牌或支付,完美地扮演着一个技术尚可、运气欠佳的角色。她甚至在林永年一次关键性的诈唬时,适时地流露出一点惊讶和钦佩的表情,虽然转瞬即逝,但足够被他捕捉到。
林永年很满意。他觉得一切都在按他预想的剧本上演。苏晓的顺从是他稳固的基础,沈冰那点小小的、不服输的反抗,则给这场狩猎增添了更多乐趣。他甚至开始在心里盘算,等会儿牌局结束,是该先“安慰”一下输了不少的苏晓,还是该趁势对沈冰提出喝一杯的邀请,进一步敲打或者说“安抚”这颗不太安分的心。
又一局牌到了关键时刻。台面的筹码已经堆成了小山。林永年手握一对K,这是他今晚拿到的最好的起手牌。他强压着心跳,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下注尺度,引诱着,铺垫着。公共牌发出,有A,有杂色,局面变得复杂。
沈冰在庄位,一直跟注到最后。现在,只剩下他们两人对决。
林永年深吸一口气,将面前差不多一半的筹码推了出去,一个足以让任何虚张声势者退缩的数目。他紧紧盯着沈冰,试图从她脸上读出蛛丝马迹。
沈冰没有立刻动作。她微微蹙着眉,看着公共牌,然后又看了看自己仅剩的两张底牌。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,包间里静得能听到中央空调轻微的送风声。她的手指不再轻叩桌面,而是安静地放在那里,左手,就在她自己的大腿旁边,离桌沿很近。
然后,林永年注意到,苏晓的右手,原本也放在桌下的阴影里,极其缓慢地,向沈冰那边移动了一寸,或许两寸。她的指尖,在垂落的桌布掩护下,轻轻碰了一下沈冰放在腿侧的手背。
只是一个瞬间的接触。
沈冰眉宇间那点微蹙松开了。她没有看苏晓,目光依然落在牌桌上,但嘴角似乎有极淡、极淡的一丝弧度,不是笑,更像是一种……确认。
她抬起眼,迎上林永年探究的目光,然后将自己面前所有的筹码,从容地、平稳地,全部推入了彩池中心。
“All-in(全下)。”她的声音依旧平静,却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,漾开无声的波纹。
林永年的心脏猛地一缩。All-in?她凭什么? bluff(诈唬)? 还是真有逆转的牌?他的大脑飞速运转,计算着概率,回忆着之前的每一张牌,每一个动作。那对K在他的掌心里变得滚烫。他不由自主地看向苏晓,想从她那里得到一点提示,哪怕是一个眼神。
苏晓却正低着头,专注地看着自己面前所剩无几的筹码,手指轻轻绕着水晶杯的杯脚,一副爱莫能助、自身难保的模样。
压力完全来到了林永年这边。他犹豫了。这对K,此刻重若千钧。沈冰那过于平静的表情,那不合常理的all-in,还有刚才桌下那若有若无的一瞥……他忽然觉得,自己好像漏掉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。一种脱离掌控的感觉,像细小的冰针,刺破了他精心维持的自信。
他思考了足足一分钟,最终,喉结滚动了一下,声音有些发干:“我弃牌。”
他将那对宝贝KK,面朝下,扔进了废牌堆。一种挫败和恼怒交织的情绪涌上来,但他强行压了下去,告诉自己这是谨慎,是高手的选择。
沈冰没有亮出她的底牌。她只是静静地将那座巨大的筹码山揽到自己面前,动作优雅,没有丝毫得意。荷官开始整理牌桌。
林永年忽然很想抽一口雪茄,却发现不知何时已经熄灭了。他有点烦躁地将其摁在水晶烟灰缸里。为了缓解尴尬,也为了重新找回主动权,他身体前倾,手臂越过小半个牌桌,故作轻松地去拿放在沈冰那侧的银质打火机。
这个动作,让他的视线得以短暂地穿透桌面上方的空间,瞥向了那片被厚重桌布覆盖的阴影区域。
时间在那一刻仿佛骤然减速。
他看见,牌桌之下,那片本该属于个人私密的空间里,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是苏晓的右手,和沈冰的左手。
EV扑克十指紧密地交缠着,苏晓的拇指,正轻轻地在沈冰的手背上缓缓摩挲着。那是一种极度亲昵、充满安抚和默契的姿态。它们就那样静静地、坚定地交扣在那里,存在于他所构筑的竞技场的正下方,存在于他自以为是的掌控王国的最底层。
林永年的动作僵住了。伸向打火机的手停在半空,指尖距离冰冷的金属只有几公分。一股寒意,比空调冷气更刺骨百倍,从他的尾椎骨沿着脊柱猛地窜上天灵盖,瞬间冻结了他全身的血液。
原来那些眼神,那些细微的动作,苏晓的顺从,沈冰的清冷,她们之间所有他读不懂或自以为读懂的情绪流转……答案竟如此简单,又如此残酷地隐藏在这里。
猎人?
他忽然想起自己刚才还在心底嘲笑着那些即将落入陷阱的猎物。
喉咙里泛起一股浓重的铁锈味。
他极其缓慢地、几乎是凭借肌肉本能地缩回手,坐直了身体。背脊僵硬地挺着,试图维持最后一点摇摇欲坠的体面。
荷官询问是否开始下一局。
林永年没有回答。他的目光空洞地落在那些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的彩色筹码上,它们此刻看起来如同孩童的积木般可笑。
原来,猎人与猎物的位置,从来不由手中的筹码决定。
牌局仍在继续,只是对他来说,已经结束了。